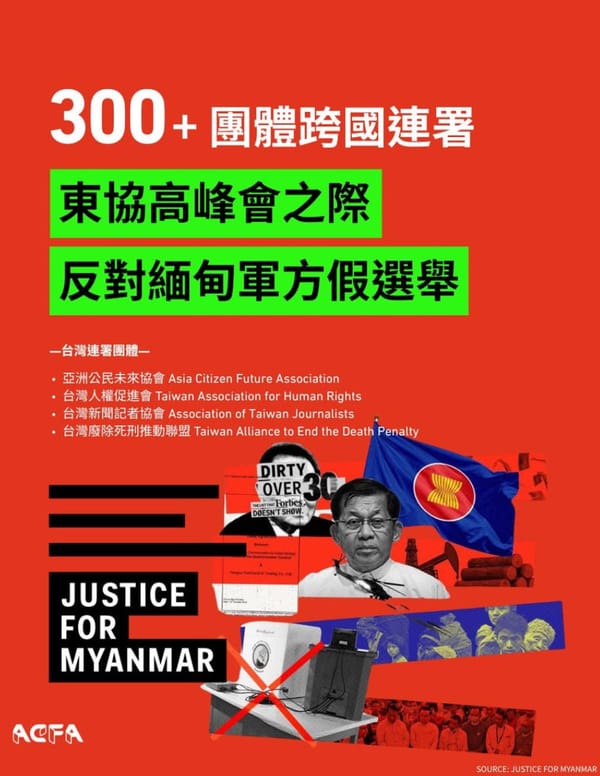【座談紀錄】當真相被噤聲,我們如何支持那些努力發聲的緬甸記者?

(紀錄者:Shin Yu)
2025年4月,亞洲公民未來協會(ACFA)舉辦「當緬甸震災真相被噤聲,我們該如何發聲?—台灣獨立記者在緬甸戰地的視角」講座,邀請長期深耕緬甸議題的獨立記者楊智強,分享他近幾年在緬甸戰地的實地見聞,以及當地328大地震後的媒體概況。
楊智強採訪緬甸的資歷長達12年,他的報導常見於《報導者》、《公視》、《轉角國際》等,2024年另與緬甸獨立記者共同創設台緬獨立媒體平台《邊境之眼》。
2025年3月28日,緬甸發生芮氏規模8.2的大地震,超過數千人罹難,然而,這場災難的真實情況卻難以傳達至國際社會。在緬甸軍方政權的嚴密控制下,當地災民難以傳訊、外國媒體難以進入災區,新聞自由受到嚴重限制,導致災情與援助資訊無法有效傳遞——此刻,扮演關鍵角色的其中一群人,是那些冒著風險聯繫外界的緬甸獨立記者,以及願意為緬甸發聲的國際社會。

為何深耕緬甸議題?為何成立台緬媒體平台《邊境之眼》?
2015年,楊智強第一次來到緬甸,當時正值翁山蘇姬上台,他因採訪當地選舉開始對緬甸產生興趣,後來羅興亞危機爆發,因此又去了羅興亞人所在的緬甸若開邦與孟加拉三趟。2023年,他自台灣非營利媒體《報導者》離職,繼續專注緬甸議題;而緬甸自2021年軍方政變以來,新聞資訊流通受限,有些外國媒體偶爾能深入反抗陣營採訪,但幾乎沒有中文媒體的身影,這也是為何他認為持續報導緬甸新聞是相當重要的工作。
2024年,楊智強與緬甸獨立記者成立媒體平台《邊境之眼》,這是「無國界記者」支持的一個計畫。「我們跟當地的獨立媒體合作,買他們的版權,由緬文直接翻成中文。」
「華文世界很少真的進入緬甸報導的媒體,大部分都是中國官媒、外媒報導中譯,或者是評論,也幾乎都是關於詐騙的主題。更滑稽的是,關於『號稱緬甸內部的第一手資訊』,很多甚至不是來自真正的新聞媒體,而是來自中國的直播主,點閱率都超級高。」
緬甸因長期內戰,資訊來源混雜,楊智強將當地資訊傳播光譜簡單分為四類:
- 反抗陣營自有管道:如「Cobra Column」這樣的組織不僅打仗,也製作影片、發佈聲明,雖然具傳播功能,本質仍屬行動者。
- 支持反抗陣營的行動者媒體:如「Voice of PDF」,擁有鮮明立場,
- 緬甸本地媒體與記者:每間媒體立場不同,如《The Irrawaddy》相當聚焦戰事、《Frontier》報導面向較廣。這些媒體雖具獨立性,依舊存在各自的偏好。
- 國際媒體:以外部觀點報導緬甸局勢,立場相對中立,但可能缺乏深入前線的脈絡。
在緬甸以外的地區,報導者與行動者的本質明顯不同;行動者是倡議、推動一件事情,記者是報導一件事情。但在緬甸,記者與行動者的界線有時候相當模糊。楊智強強調:「記者使用素材時,必須辨識各自的傾向。我非常清楚自己是記者,而不是行動者。」
緬甸震災的資訊怎麼流通?
緬甸大地震後,軍方隨即在國內外封鎖訊息、取消觀光簽證,造成資訊斷流,其中,震央實皆省幾乎無法聯繫,楊智強僅能靠熟識的曼德勒朋友轉傳資訊。
軍方嚴密控管震災與死傷人數的消息,連前往當地單純救災的人,也必須向軍方拿到許可證。震災的死傷人數嚴重淡化,以寺廟為例,「緬甸有很多寺廟,裡面除了和尚、尼姑,還會收容很多來來去去、流離失所的人。地震前,軍方不知道每間寺廟的實際人數,地震後,他們也不希望死傷人數太多,因此傷亡人數統計有很大的落差。像我知道的某座寺廟,官方數字只報了四分之一的死亡人數。連寺廟人數都無法掌握了,更不用說震災各地區。」
在這樣的狀況下,國際媒體的積極發聲也很重要。例如,美國總統川普近期裁撤了「美國之音」(VOA)在緬甸的頻道,但震災之後,英國BBC透過接管「美國之音」的頻道,應對緊急的資訊需求。
緬甸議題頻遭誤解與汙名化
然而,在緬甸向國際求援的同時,台灣卻出現另一派歧視性言論,來自近年緬甸詐騙園區的負面新聞與形象。針對緬甸遭到汙名化的現象,楊智強分享,「其實,緬甸的詐騙園區裡幾乎都是中國人,不是緬甸當地人,因為後者的口音騙不到人。中國的不法份子在緬甸邊境這樣權力真空的地方,興建詐騙園區,並與緬甸軍閥往來。」
「今年初,中國與泰國宣布聯手打擊KK園區,那時我剛好在緬甸邊境。緬甸有一支部隊叫做邊防軍,他們發佈新聞稿,表示自己衝進多少園區、救了多少人,但是當地人都知道,他們就是一直在保護KK園區的軍閥。」
「緬甸自從獨立以來,不同民族都有不同的地方武裝勢力,長期以來,各自衍生出各字的賺錢方式,有的被軍方政權招安,有的要自治,有的親中國。各地勢力都有自己複雜的脈絡,有時候立場還會變化。」因此,將緬甸軍方政權、各地軍閥、緬甸人民分開來看,才能更了解當地議題的脈絡。
採訪緬甸時是否曾遇過威脅?
談到威脅,楊智強表示自己沒有直接受到限制,但在戰區採訪,常常得繞道、接受盤查。他提到,緬甸邊境各檢查哨標準不一,今年2月左右,正值中泰聯手打擊詐騙,泰國警察常要求檢查護照、盤查身份,「所有外國人跟行李都要下車,問完再載你去巴士站。現在在美索,聽說要有美索的泰國人來保你,才可以入境。」然而,也有人的簽證直接被拒絕的案例,標準並不明確。
他表示,警察對東亞面孔的警戒會比西方面孔的警戒還要高,外國記者面臨的風險相對較低,真正可能遭受危險的是緬甸本地記者與翻譯:「他們一旦被抓,就可能被送去當兵打仗,還會被記上案底。那些媒體執照已被撤銷的媒體工作者,更是危險,即使人在鄰國(例如泰國),只要被抓,就可能被遣返。」
然而,即使如此,許多記者都還是想回去緬甸採訪,讓他非常感動。
不願放棄的緬甸記者
楊智強表示,在川普縮減USAID之前,緬甸獲得的援助雖然沒有很多,但還是有很小一部分會分配給獨立記者。然而,在各項資金紛紛被裁撤、震災打擊之下,記者面臨越來越嚴重的經濟困難。他透露,《邊境之眼》合作的其中一位緬甸記者,近日甚至向他借一千美金度日。「這些已經是能夠接觸國際資助的記者,現在連一千美金都要借。其他沒資源的媒體工作者,說不定都已經消失了。」
「外國媒體只能偶爾進去緬甸報導,很多沒開放的地區,更不可能深入,一定要靠這些記者才能傳出來。連這些記者都無法做報導的話,那緬甸的許多黑幕不可能有被看見的一天。」他說:「緬甸的獨立媒體與記者,真的已經到生死存亡的關頭。」
楊智強說,這位記者本來是BBC在緬甸的記者,後來因政變而被迫離職。「我問他:『不當記者的話,你要做什麼?』他說:『我會繼續當,因為我不知道要做什麼。』他賣掉奶奶的土地,自己做媒體,也因此跟家人決裂。本來,他想繼續待在當地,但他弟弟被逮捕、遭判死刑,他因此逃到泰國;即使弟弟改判無期徒刑,他還是不敢回去。」

國際社會如何支持當地媒體與記者?
楊智強說,國際媒體扮演著重要角色。「國際聲援通常不會立竿見影,但當你連國際聲援都沒有的時候,連『竿』都沒有,獨裁者就會鬆一口氣。國際聲援可能無法馬上改變某個政權或局勢,但這項壓力的長期存在,有戰略上的必要性。」例如,「無國界記者」(RSF)有支持緬甸媒體工作者的專案,「像是在日本蒐集二手採訪器材,送進緬甸,提供當地記者使用。」緬甸氣候潮濕、溫差很大,鏡頭容易起霧,器材耗損率很高。
「連我自己進去採訪,器材都很容易壞掉,所以器材的支援其實非常重要。我認識的很多本土記者,都是土法煉鋼,互相出借器材一兩週,以應對資源不足的問題。他們沒有像台灣記者協會這樣比較大的組織,而是一小群一小群互相幫助,這樣對他們來說也比較安全。」
由於軍方嚴密控管網路,緬甸記者還需自己付費另買VPN。然而,2024年5月,緬甸正義組織(Justice for Myanmar)公布一份報告,指出緬甸軍方與中國資安公司合作,蒐集生物特徵與VPN,這讓記者翻牆的難度增加了。而緬甸因內戰遭受國際制裁,大部分信用卡無法使用,因此花錢上網變成越來越奢侈的一件事,「有時候你買了這個VPN,隔天就被軍方查到,又要花錢買另一個VPN。」
在這樣的背景下,Starlink 網路服務本為少數可用的網路工具,近年卻因詐騙集團濫用,泰國開始打擊擊 Starlink 使用者 ,也連帶影響緬甸這些亟需網路的人。
而台灣有許多緬甸相關團體,台緬記者有無可能透過此網絡獲得協助呢?楊智強認為:「台灣團體在賑災部分比較沒問題,但台灣媒體要進去災區,都進不去。當地網路傳輸量很低,當地人要把一些比較適合的畫面傳回來也很困難,對新聞報導幫助相對有限。」
透過這次精彩的講座,許多聽眾更了解緬甸震災後的現況,尤其是當地媒體與記者的處境與需求。楊智強以自身見聞與創立平台為例,更啟發了大眾未來以其他多元的方式支持緬甸獨立媒體與記者的可能性。